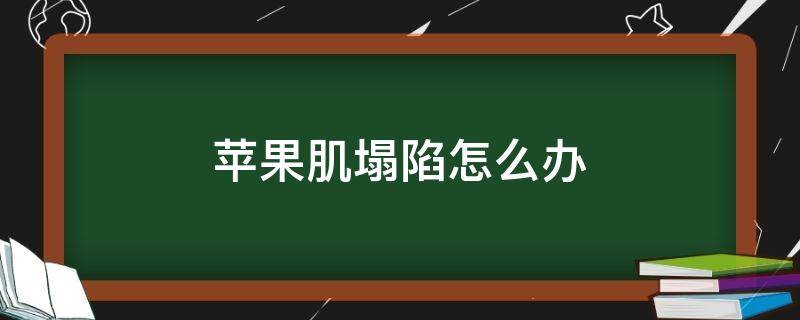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
无声的死亡
事情不太妙。6月2日,黄中原的妻子在凌晨惊醒,发现另一个房间正在直播的丈夫躺在地上,身体已经发凉,地上满是烟头和瓜子皮,墙角堆着啤酒瓶。1个小时前,黄中原还在直播喝酒,屏幕里的脸因醉酒涨红,礼物特效和弹幕飞屏。

黄中原直播的房间。焦晶娴/摄
在赶往黄中原葬礼的路上,主播吴力觉得事情太诡异。这是他近1个月参加的第二场主播的葬礼。上一场黄中原也参加了。没人想到黄中原会出事。
他们都靠直播喝酒挣钱,有主播一晚上喝10多斤白酒,和他们相比,黄中原喝的并不多。吴力回忆,黄中原多数时间是“陪粉丝聊天”。
黄中原的妻子告诉记者,黄中原死于呕吐物窒息。
每晚她都会去丈夫直播的房间看一眼,怕他出事。黄中原日常工作是在镜头前,大口咽下白酒、生鸡蛋、蝌蚪,甚至烟头。晚上直播喝酒,喝到凌晨两三点才下播。
5月底,黄中原的妻子一直在医院照看生病的孩子,只能通过电话和短信“监视”丈夫。出事前一天是儿童节,黄中原来接妻子和孩子出院。
在医院旁边,黄中原习惯性地买了张彩票。他喜欢买彩票,年轻时曾在“快三”彩票上投了几万元,没中过奖。但他仍期待着暴富,“钱比命重要”,他在直播房间墙壁上用粉笔写上这句话。
傍晚回家,黄中原只喝了点小米粥就上楼准备直播。因为长期喝酒,黄中原的胃不好,只能吃些软的东西,他越来越瘦,174厘米的个子,只有102斤。
6月1日晚上,4岁的儿子睡前叮嘱爸爸,“爸爸你少喝一点,我先睡觉啦,明早我要看见你在我身边”。
他们住在二层小楼里,房子是去年黄中原借了30多万元新盖的。一层装修得很精致,门口的木质秋千是他手工做的,墙上挂的国画是他画的,画上一个孩童悠闲地骑在牛背上。午夜12点,黄中原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入睡。
楼上则是没装修的毛坯房,黄中原在其中一间屋子直播。屋里只有一张床、一套桌椅和两盏直播用的灯。
当农田和树林隐入深夜,黄中原家的灯还亮着。
黄中原的邻居、一位60多岁的大爷还在睡梦中。他曾在半夜刷到过黄中原的直播,看到黄中原猛灌啤酒,他没看两眼就关了,“这东西没啥价值。为了挣钱不要命了” 。黄中原在村里名声不太好,就连不看直播的老人,也知道他吃老鼠。
凌晨4点左右,邻居大爷突然被黄中原家人的电话叫醒,让他帮忙找村卫生室的医生。
“中原不行了”,电话里说。
没人能说清楚,黄中原当晚到底喝了多少酒。平台上已经找不到这场直播的截图或视频。有粉丝后来告诉黄中原的妻子,黄中原喝了两三瓶白酒后,有“10多分钟大喊大叫”,然后直播就终断了。一名粉丝称,弹幕里有人说“打120吧”。但最终没人打出这个电话。
黄中原出殡那天下着大雨,粉丝和朋友把他的棺木抬上了山。

黄中原画的画。焦晶娴/摄
死亡的循环
15天前,吴力和黄中原参加“三千哥”王兆丰的葬礼,主播来了好几桌,还有人试图直播。
相比黄中原,王兆丰直播时更亢奋,在圈子里朋友很多。王兆丰经常在直播中喝醉,他把醉酒也当作表演的一部分。有次喝多了,他躺在洒满彩色纸片的地上打滚,摇晃着跳舞。粉丝在屏幕上高呼“666”“有两下子”。姐姐王丽打电话让他下播,他反而把她拉黑。
5月17日凌晨,在直播中喝下7瓶白酒和3瓶红牛后,他就一直趴在桌上,随后直播中断。他平时一个人在乡下的房子里直播,妻子带着孩子在县城上学。下午被村民发现时,他已经死亡。
吴力回忆,王兆丰性格大大咧咧,为人仗义,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他自称“互联网第一能喝”,为了显得夸张,他用比脸还大的巨型酒杯装酒,把头埋进去喝。但他的朋友和家人说,他真实的酒量只有半斤。
王兆丰生前直播的房间里,由于担心扰民,窗户被全部封死。墙上贴满了A4纸,上面写着“我命由我不由天,灭你只在挥手间!”
他初中毕业就进社会闯荡,卖过水饺、做过猪脚饭,后来做生意赔了钱,2020年为了还债做直播,有不少“大哥”“大姐”(财力雄厚的打赏粉丝——记者注)给他打赏。
今年年初,王兆丰终于在老家买了套房子。王丽劝弟弟转行开个小店,“总归要回到现实生活中来”。但王兆丰已经离不开直播。他过年吃饭时也拿着手机,“走到哪播到哪”。
王兆丰去世后,家人从他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一沓电话卡。每次被平台封号后,他就用这些新号码注册小号继续播。
去年9月,王兆丰因直播中饮酒过量住进了ICU,诊断结果包括急性酒精中毒、急性胃黏膜病变、肝损害等,直到出事前,他还在喝中药。
去年出院后没多久,他又开始在直播中灌白酒。他觉得自己进ICU是因为喝了假酒。一名粉丝回忆,王兆丰曾在直播中说,“做主播光宗耀祖”。
网上流传着王兆丰生前最后一场直播的截图,他趴在桌上,弹幕里有人开玩笑,“直播睡觉月入百万”。
王兆丰的葬礼上,王丽记得黄中原一直“愣愣的”,盯着王兆丰的照片不说话。她用手指着黄中原,流着泪说:“尤其是你,千万不要再喝了。”
王丽也看过黄中原的直播。她知道黄中原和弟弟一样喝酒“实诚”,从不兑水,甚至总是压着不吐。
“他都点头了。他都答应我了。”王丽对记者说。
15天后,王丽得知黄中原去世的消息。“听到这个,我真的挺生气,好恨他们。”她的声音微微颤抖。
半年前,江苏盐城患肺结核的主播“耀子”去世,也和直播中长期饮酒有关。那时王兆丰也参加了他的葬礼。
没人知道第一个因直播而死的主播是谁。
2017年11月,高空极限运动第一人、在花椒直播等平台上进行高空表演的“网红”吴永宁,在湖南长沙华远国际中心攀爬时坠楼。
2020年6月,沈阳一名“大胃王吃播”王先生在准备直播时突然出现身体发麻、头晕目眩等症状,在医院连续抢救7天后去世。
2021年3月,吃播网红“泡泡龙”离世,生前体重已达320斤。
2021年10月,网红“罗小猫猫子”在直播中喝“敌草快”自杀,经抢救无效去世。直播间有网友起哄让她“喝下去”。
今年5月27日,312斤的网红“翠花”在减肥训练营离世。 除了白天训练,她还会在晚间直播,当着粉丝的面加练。
某直播平台财报显示,2023年该平台第二季度收入277.44亿,平均日活跃人数达3.76亿,再创历史新高。线上营销服务和直播是主要营收来源,分别占52%和36%。
在巨大的收益面前,一些主播和流量赛跑,直到死亡。

吴力用头磕烂的红牛,保存在冰箱里。焦晶娴/摄
奇观的诞生
这些为流量越来越拼命的主播,让观众的兴奋阈值不断提高。
“那些才艺,什么唱歌、跳舞软绵绵的,没意思”,54岁的杂货店店主李秀莲对记者说。她喜欢“狠PK”那股子热闹劲,主播声嘶力竭地拉票,“屏幕上的字唰唰唰往上飞”。她平时看店无聊,就会点进直播间。
主播也会用话术刺激观众,“有没有家人救救我” “大家守一下塔”。
李秀莲喜欢一位30岁出头、长相帅气的男主播,每次听着对面主播骂得难听,自己支持的主播不断求救,“恨不得我上去帮他拉票”。她很清楚主播和现实中的朋友不一样,“网上有什么真朋友?但被气氛带进去,管他真朋友假朋友,有钱就支持他”。
看到对面主播输了做惩罚,李秀莲从不会心软。有次李秀莲支持的主播赢了一个女主播,惩罚是喝6瓶水,然后把自己绑在树上,两小时不能动。最后那个女主播尿了裤子。
李秀莲心中闪过一丝内疚。她知道那个女主播是单亲妈妈,当时“也有一点心疼的感觉”。但她马上被满屏的“大姐威武”字幕,转移了注意力,“被那个气氛一带,啥都忘了”。
接受记者采访的“狠PK”观众中,有人说自己刷礼物就像是“买张动物园门票”,有人把看惩罚当作“压轴节目”。
他们表示,PK过程中最刺激的环节,是“大哥”“大姐”出手时。巨大的特效占满大半个屏幕,弹幕清一色的“感谢大哥/大姐”“大哥/大姐威武”,将直播间的气氛烘托到顶峰。所有人共享“碾压”和“反转”带来的快感。
出手越阔绰的“大哥”“大姐”,平台显示的等级数字越高。砸钱是最快速升级的方法,一开始升级不难,从1级到10级只用20多元。从40级到50级,所需金额已经达到了100多万元。升到60级的人屈指可数,因为需要消费2000万元。他们被称为“神豪”。
李秀莲虽然不怎么刷礼物,但几乎每天都看那位主播。花了两年,主播把她拉入粉丝“家人群”,她觉得“倍儿有面子”。
群里的粉丝都把“守护主播”当作共同使命,有人说自己月底才发工资,拜托别人“好好守护”。有人开养殖场,说“等我这批猪出了,我来坚守”。为了表达感谢,主播会给群里的粉丝寄些小礼物,比如家乡的农产品。
有时刷礼物也是种发泄。一位26岁的年轻“大姐”,半年内刷了120万元。她的家境很好,不愿透露自己的工作,她告诉记者,自己平时工作强度不高,一般都是白天戴着耳机听直播,晚上陪家人。
心情不好的时候,她看某个主播“长得不顺眼”“嘴这么贱”,就会故意给这个主播的对手上票,为了看他输了做惩罚。有次直播惩罚是1000票吃一个鸡蛋,她讨厌其中一个主播,就给对面主播上了10万票。
“没有PK我肯定不会上票”,她承认,“你一旦看了,那种氛围就像吸毒一样,会上瘾的。”她觉得看直播就像购物,“有些人不上票只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,而不是因为理智”。

吴力直播的房间。焦晶娴/摄
赌徒的命运
吴力很感谢那些“大哥”“大姐”。他们决定了自己在“赌局”里的命运。
每次直播的PK倒计时开始,屏幕一分为二,主播的票数被量化成一道光条,主播也叫它“血条”。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,吴力嘶吼着拉票,劣质话筒“滋啦滋啦”直响。
当PK结束,自己的票数超过对手,“冠军”二字跃上屏幕,吴力会双手合十举过头顶,喊“谢谢大哥!兄弟们把解气打在公屏上!”鞠躬时,头快要低到地上。
每次PK他输了,做完惩罚,有人佩服,“你也是个狠人,关注你了”。有人讥笑,“哈哈,炸熟了”。有人对惩罚不满意,“不够狠,再加20个”。
渐渐地,吴力认为“狠”才能帮他赢得尊重。“我的心理就像那些挑战冰山的,徒步的。我挑战的东西,没人能完成。我完成了,就有一种成就感。”
粉丝的回应让他更加确信这点。有个经常刷礼物的“大哥”,自称是某集团老板,私信夸吴力,“感觉你跟我年轻时一样,打拼的时候有一股韧劲儿,输了也不服输”。
如果不笑,吴力看起来很不好惹。他头顶有块拇指大的地方,刚长出嫩肉,他用那里砸碎过啤酒瓶、磕烂过红牛罐。肚子上形状不规则的疤是鞭炮炸的。手臂上有密密麻麻隆起的、烟头烫的疤痕。
他嚼过玻璃碴,含过鞭炮,刀片划过舌头,这让他失去过半个月的味觉。去年6月,因为把鞭炮夹在耳朵上面,他感觉耳朵里疼了两天,去医院被诊断为耳膜穿孔。
他住在国道边的一个修车行楼上,货车的轰鸣和修车的噪音是他直播最好的掩护。
从黄中原葬礼上回来,二女儿的班主任发来信息,催他交4900元的学费。他一个人拉扯3个女儿,每月要还1万多元的网贷。即使是大年三十、女儿们的生日,吴力也没停播过。两个朋友因直播离世后,每天晚上8点,吴力还是准时开播。
3人最后一次聚会是今年2月,吴力和王兆丰去找黄中原玩。三门峡的高阳山上,风还带着寒意。吴力看着远远被落下的两个朋友。他们气喘吁吁。“身体都×××喝废了”,吴力开他们的玩笑。
在山顶,他们拍了张合照。照片里,黄中原站在中间搂着他们,吴力和王兆丰在旁边竖起大拇指。
王兆丰和黄中原相继离世后,3人的合照广为流传。主播群里有人发语音“@”吴力,“(你)能不能死?新闻还没过呢”。直播间里也有粉丝提醒他,“就你还活着,你要注意了”。
吴力经常提到“几率”,他现在不接喝酒的惩罚,不玩“点单”(粉丝直接出钱指定主播做任务,任务的难度和礼物的价值挂钩——记者注),他觉得这样出事的“几率”会小很多。他现在玩的惩罚都是外伤,“外伤顶多是流血,去医院包扎一下就行”,他这样说服了自己。
他用身体,赌一次“天时地利人和”——正好定的惩罚足够刺激,正好“大哥”“大姐”来了,正好自己的表现让“大哥”“大姐”开心。钱就到手了。
王兆丰入行是因为做生意赔钱,黄中原读大专的时候就欠着网贷,吴力是因为网赌欠了70多万元。
直播是他们的救命稻草,他们想再赌一把。吴力告诉记者,“感觉就像是,即使我只是初中毕业,我在这里也能赚到第一桶金”。
2016年作为“直播元年”,中国大陆提供互联网直播平台服务的企业超过200家。据某家平台官方数据,2018年,中国有超过1600万人从这家平台获得收入。
相比才艺和搞笑主播,“狠PK”入行门槛很低,只需要有一部手机和一具能忍受疼痛的身体。他们管自己叫“互联网上要饭的”。
《中国网络表演(直播与短视频)行业发展报告(2022-2023)》显示,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播中,95.2%的人月收入为5000元以下,仅0.4%的主播月收入10万元以上。
为了研究短视频/直播主播的线上劳动特点,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吕鹏从2015年起关注“草根”主播,和其中的70多位进行过访谈。
他发现,平台背后的隐形机制会让新主播不断尝到甜头,但绝大多数“草根”主播的成功只是“昙花一现”,由于缺乏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,他们无法持续生产优质的内容。他访谈的部分“草根”主播,直播生命周期只有几个月。
从云端坠落
吴力从没体验过当“大主播”的感觉。但他的朋友黄中原从流量的云端狠狠摔下来过。
7年前,黄中原还是个在郑州上大专的学生,19岁,美术专业,喜欢捣鼓画笔和文玩。他家里至今还存着他曾在学校师生技能大赛中,荣获素描一等奖的奖状。
黄中原第一个“小火”的视频,是在学校的超市里,他在镜头前随手拿起一瓶白酒,一口气灌下去,再把瓶子放回去。那个视频让他涨了几千名粉丝。
此后黄中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。李飞是黄中原的同学,也是他的“摄影师兼经纪人”。李飞觉得,“火烧鸡”事件是黄中原人生的转折点。
那是一条2016年拍摄的视频,视频里,黄中原先把杯中的酒点燃,再蘸取燃烧的酒点烟。“喝杯火酒”,他端起带火的酒往嘴边送,手一歪,带着火焰的酒洒在裤裆上,火苗瞬间上窜。黄中原痛苦地叫着,“快来打!快来帮我!”他惨叫着跑出屏幕。
这段视频播放量超千万人次,点赞量五六十万,让黄中原涨了几十万名粉丝,卖假鞋、卖二手组装机的纷纷找他打广告,好友申请能翻几页。
李飞说,这其实是一场预料之中的“意外”。
着火是计划内的,第一次拍摄,火苗打一下就灭了,“要的不是这个效果”。第二次拍摄,由于裤子上洒了两次酒,火势开始不受控制。由于事先穿了防护的裤子,黄中原的腿没事,但火苗把他的肚子烧伤了一大片,他在医院躺了两天。
但这让黄中原觉得“很值”。“火烧鸡”事件后,他有了名气,1个月最多能挣5万元。
他对自己越发狠了,李飞说:“他对我说过,摄像头一开,给他什么他都吃。” 黄中原在镜头前吃下过生鸵鸟蛋、活蝎子、蝌蚪、老鼠。
有次他把燃烧的烟头都吃了。“是铁粉就双击,双击双击再双击。”他在镜头前表情痛苦地说着。
不到半年,因为直播内容违规,黄中原被平台多次封号。
几年下来,黄中原没存下什么钱。有时候一晚上赚的钱还不够买酒。
李飞回忆,黄中原对钱一直没什么概念,“具体怎么花的我也不知道,就是还网贷,然后吃吃喝喝,玩老虎机”。大学的时候,黄中原买苹果手机、请朋友吃饭,借了不少网贷。
去年盖房子的时候,黄中原只凑出1万多元,借了30万元的贷款。
吕鹏发现,自己接触的大部分“草根主播”,都会堕入到“挣钱-挥霍”的循环。其中一些是初高中刚毕业,很早接触短视频,没有金钱的概念。“有人说他1个月十几个‘W’(代指“万”——记者注),但绝大部分都挥霍了。钱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”
吕鹏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:底层气质让这些主播火起来,但最终也会制约他们的发展。
其实黄中原不喜欢喝酒。有时他会大半天都趴在画纸上。他也拍过不喝酒的视频。他拍过自己炒家常菜,做过旅游照片的集锦,拍过自己在卫生纸上画的西游记人物。他还拍过搞笑段子,坐在公交车上,头上戴一块榴莲皮,脚踩在砖头上,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。黄中原的妻子回忆,“他感觉没有流量,没有人欣赏”。
在他做菜的视频下面,有人评论,“关注你是因为喝酒,美食博主取关了”“你绝对在备孕”“赞没有原来多,不反思一下吗”“用酒熬的粥吧”。
后来,他的视频封面又变回不同度数、包装鲜艳的劣质白酒。
成为“狠人”
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学者董晨宇把直播行业比作“黑洞”,对于主播来说,“不断地吸引他们,管理他们,规训他们”。
他曾经在一个平台对多位女主播进行过1年的观察研究,他认为直播背后的“非道德经济”伤害的是从业者的价值观。这种伤害是隐形的,被短期的盈利所掩盖。
3年前刚开始直播的时候,吴力还会因为紧张结巴。那时他不怎么懂网络,常年在新疆的戈壁滩上开货车,满眼都是黑色的山丘和沙土,没有草,也没有信号,打电话要爬到半山腰。他们跟着工地跑,空闲时就打斗地主,或者把矿泉水瓶盖里塞上纸片,做成象棋。有次他在工地上受了伤,在病床上休养期间接触了网赌,欠下了七八十万元的网贷。
他四处打听赚快钱的方法,朋友让他试试直播。
吴力开始每天都发一个喝酒的短视频,混着鸡蛋喝,混着料酒和油喝,或者跑到富士康门口、在下班的人流中喝,“想各种方法博流量”。
不到1年,吴力一次能喝下的生鸡蛋,已经从20个涨到了250个。
接着是学习“拉仇恨”,PK时两个主播骂得越凶,“大哥”“大姐”越有上票的欲望。
他还砸坏过空调扇、吊灯、新买的发财树。他也不想砸,但他没有话语权。惩罚是“大哥”定的。
他的冰箱里还堆着几十个砸开了口的红牛,他不舍得扔,“一罐6块钱呢”。除了自己喝,他把破的口子朝上,装回箱子,送给亲戚和朋友。他不好意思说是自己砸的,别人问起就搪塞说,“买来就是这样”。
在现实生活中,吴力很害怕熟人问起他在做什么。
他让女儿在父亲的职业那栏写“农民”。一次他去信用社办理贷款业务,业务员认出来了他,问他是不是那个很能喝酒的“网红”,他连忙否认。
他几乎斩断了所有社会关系。他白天睡觉,晚上直播,很少出门。
戈壁滩上开货车那种和世界“脱轨”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吴力已经很久没回过家,连续3年,过年他都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开着直播包饺子。
因网赌欠债后,吴力到处借钱,亲戚都对他避而不及,妻子和他离婚。于是他离开家,在县城租了房子专心做直播。走前,他在父母面前重重磕头,“不挣到钱,就不回家”。
他躲进了直播,直播也让他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。吴力有时会去以前买的宅基地看看。那是他原本准备盖房子的地方,现在被拿来种菜,黄瓜、苋菜、小青菜在太阳下炙烤。
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。
他希望直播能把他带出赌博的阴影。事实证明,直播确实帮他还了一些债,但也让他的生活陷入了新的阴影。
现在吴力害怕回家,害怕亲人问询的眼神,以及邻里间的闲言碎语。有次他开车离开,从后视镜里看到邻居对着他指指点点。侄子曾经在直播间举报过他,村里的小孩用他的网名编顺口溜,“跟着××混,三天饿九顿”。
吴力的父母都是农民,两个老人操持15亩地,收完西瓜,凌晨3点就要推着三轮车上村口卖。歇不了几天,又要收胡萝卜了。
吴力的母亲是个大嗓门,60多岁了,她回忆,吴力回来总带着一身伤,有时还要借父母和亲戚的身份证注册小号。即使是这样,她还是觉得吴力是个“好儿子”,相信他“迟早有天会回头”。
女儿们也觉得吴力是“好爸爸”,虽然吴力平时邋里邋遢,白天眼睛总是困得睁不开。吴力周末都会带着女儿下馆子。他从来不在女儿面前骂人。他会坐在女儿旁边,监督她们写作业,虽然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直播夺走了吴力的睡眠和大部分的精力,很多事情他无力改变。他的小女儿只有4岁,平时是爷爷奶奶带。二女儿上小学四年级。
大女儿上初二,最懂事,也最担心他的身体。有时候吴力账号被封停播,她会很开心,“至少不用再受伤了,也能好好休息”。
大女儿睡得浅,她知道,一缺钱,父亲的直播时间就会拉长。去年有段时间,她的学费很难凑齐,父亲凌晨5点才下播。她的目标是努力拿奖学金,虽然只有几百块。
吴力最怕女儿们看到他的直播。刚开始,吴力会在直播间里叮嘱,“在看的不管南南还是甜甜,早点睡”。后来“活儿”越来越狠,他专门检查过女儿们的关注列表,以防她们看到自己。
平时吴力在客厅直播,他会关上女儿们的卧室门,叮嘱她们不要出来。如果她们出来上厕所,吴力就立刻停下直播。
这只是种心理安慰,嘶吼声和鞭炮炸开的声音还是能传进卧室。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、五下。二女儿捂住耳朵,笑嘻嘻的,预报着鞭炮响起的次数。这是她玩过多次的游戏。
但在父亲面前,她们装作不在意,因为不想给父亲压力。有一次吴力下播后过来看她们,他的胳膊用纸巾缠了一圈,已经被血染透。吴力走后,小女儿才哇的一声哭出来。
小女儿有次忍不住,哭着对吴力说,“爸爸,你别喝了呗”。吴力的眼泪瞬间落下来。
家人的哀求撕扯着主播的心。董晨宇访谈的主播中,很多是单亲妈妈。一位主播告诉董晨宇,她平时在儿子熟睡后,才在客厅支起手机直播跳舞。不到半年她离开了这个行业,因为儿子对她说:“我睡觉的时候,你能不能不在外面跳了,能不能陪我一起睡?”
“当时她说这话我眼泪都下来了,因为我也有孩子。”董晨宇说。
对于主播来说,平衡两个世界的生活并非易事。董晨宇认为,即使主播将经济收入作为从事这一职业的原始动机,但当工作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,他们很难消解和平衡这种失调带来的不道德感。
猫鼠游戏
王兆丰去世后,吴力在某个平台被封了6个号。黄中原去世后,吴力被某个平台“永久封禁”,俗称“封脸”。 这家平台针对高频饮酒主播进行人脸黑库识别,防止封禁后大小号替换等行为。
吴力只能换一个平台播。不过现在喝酒行为被平台集中治理,不管是哪个平台,只要有酒瓶出现,或者有人说出“酒”相关的字词,直播很快会被终止。
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、研究平台经济与网红文化的学者林健发现,目前短视频/直播平台常见的内容监管模式是,恶性事件出现,政府出台文件,平台积极执行。
出于“数据就是货币”的商业逻辑,一些平台初期会遵从“擦边球策略”,对于一些新兴的、带来一定流量、尽管有潜在问题但尚未“暴雷”的内容,采取默许的态度。一旦问题暴露,政府出台禁令、社会舆论压力增加,平台则会转过来打压此类内容。
吴力也从不断变化的账号封禁时长中,感受到了环境微妙的变化:3年前违规只是封1个月,后来则延长到1年、两年,现在则是“永久封禁”。
吕鹏在和主播们的访谈过程中,发现几乎所有主播都叫平台“官方”,这种称呼非常明显地将平台视为“官”,将自己视为“民”。
但这种管理并非强制性,双方围绕各自利益不断博弈。注册成为主播前,用户都要阅读《直播行为规范》,吴力也看过,他知道自己“每天都在触碰这些东西”“经常违规”。
于是主播和平台间的“猫鼠游戏”成为常态,主播们有各种方法逃过监管,比如花钱买一个营业执照,用来注册“传媒号”“企业号”,就可以用别人的身份证注册账号。一些被“封脸”的主播,还会选择戴着面罩、口罩继续直播。有人1年被封过30多个号,但还在直播。
也有人因为封号放弃直播。2020年,吴力的师傅顾武粉丝量创新高,结果被永久封禁,“心态直接崩了”。顾武去其他平台拍“正能量视频”,挨家挨户送米和油,在视频下面挂小黄车卖货,但“不挣钱,开销太大”。干了1年,账号解封,他又继续回来玩“狠PK”。
多位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,事实上,平台从未停止探索内容审核的最优解。在某平台,一个播放量超过200万的视频,至少经过四层审核。
政府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完善直播行业相关的政策文件。据不完全统计,2016年至2022年,近7年来国家出台了近20份涉及主播的政策文件,划定准入门槛、建立黑名单、筑牢合规底线,规则不断加码。
林健认为,目前仍延续着“出现问题-解决问题”的处理模式,监管具有滞后性。平台企业往往会迫于公共压力出台临时性治理措施,平台成为政府政策的被动执行者,而政府文件不可能面面俱到、囊括一切管理细则。
另一方面,当平台成长为小型社会,过于庞大的身躯,让毫无死角的清扫成为幻想。《中国网络表演(直播与短视频)行业发展报告(2022-2023)》统计,截至2022年,我国主播账号累计开通超1.5亿个,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.51亿,占整体网民的70.3%。有报告估计,全球每日上传短视频超4亿条。
国外一篇探讨内容审查智能化的论文指出,目前各大平台面临的内容审核的困境,是平台“不惜一切代价增长”的发展心态必然带来的后果。
“一些平台确实是太大了”,作者在论文中强调。
人生理想
进入新平台,吴力花了1个月,也没涨回原来的粉丝量。
为了吸引流量,他只能让惩罚看起来更狠一些。原来磕红牛罐,要磕七八十下才能磕烂,现在他最快5次就能磕烂。不过他的头也越来越不经磕,原来磕8个罐子头才会流血,现在磕1个就会流血。
吴力回忆自己有次因为封号换平台,为了快速积攒人气,打了一场“从没有人打过”的“生死局”:一次喝下5斤白酒,250个鸡蛋。
当时的对手是个叫倪小天的主播,1年后,吴力听到了他的死讯。
有次倪小天线下见了在直播间常给他打赏的“大哥”,吃了顿饭,又被带去酒吧,在线下接了点单,定的任务是喝酒。喝完他躺在卡位上睡觉,徒弟在旁边直播。过了一会儿,徒弟一摸,人已经没气儿了。
那是吴力第一次听说主播圈里有人喝死,他虽然感到震惊,但他不认为“大哥”有什么错,“现在(干这行)久了,没什么事儿不能理解。每个人的发泄方式不一样。只是我没钱”。
吴力每天一睁开眼,想的就是直播赚钱。他的人生两大目标是,买套房,然后买一辆奔驰车,“一定要大标的”。
他的手机铃声是“没活成想要的样子”。他开的旧车是10年前买的,车上震耳欲聋的DJ音乐中,网红叫嚷着,“输不起你就不要输,死不了你就站起来!”
他认为,混出名堂、赚到了钱,才叫“站起来”。
两个朋友离世后的那个月,他一晚上赚四五百元,少的两三百元,但上个月好的时候能有三四千元。他认为只要继续播,就能复制赚几千元的那个时刻。他从没想过回去开货车,“直播赚快钱赚习惯了”。
董晨宇分析,这种心理就像“抽彩票”,收入不稳定带来的“愿景”,是吸引很多人从事这个行业的原因。对于主播来说,“不稳定”的另一面就是“有希望”。很多主播并不会转型或学习新技能,而是只想就这样赌下去,等待下一个被流量砸中的机会。
吴力曾经做过老家的蔬菜产地代办,帮着乡亲们联系外地客商,他也想过做助农主播,但一直不敢踏出第一步。理由有很多,包括“水很深”“我没有渠道”“风险太高”。
在他看来,“狠PK”的技术含量就没那么高。
据南方都市报报道,有直播公会、MCN机构或主播孵化机构提供“PK节目效果”“10分钟PK怎么打”等培训课程,有的还教“刺激”玩法。还有人发布“怎么通过PK要到大票”“直播间PK游戏惩罚大合集”等经验帖,并教授主播维护和“大哥”“大姐”的关系。
林健认为,平台作为一个生态集合,用户、创作者、MCN机构等多元主体目前并没有积极参与到平台治理中。他希望平台和社会力量可以向“草根”主播提供一些资源,帮助他们通过更积极健康的方式实现盈利和自我表达。
吴力把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,准备明年带她们去北京的大学转一圈。
“你爸这辈子算废了,你们要好好学”,他常跟女儿们说。现在他最朴素的愿望就是好好睡一觉,“等还完债,我要大睡3天!不直播,不看手机,睡醒就吃,吃完就睡”。
“这个行业是糟糕的,但这些人只是普通人”,董晨宇在结束调研后这样总结。
最近,一批年轻的新主播也来到平台,找吴力当对手打“PK”。和当年的吴力一样,他们愣头愣脑的、弄不懂规则,又野心勃勃。
面对他们的挑衅,吴力只是宽容地笑笑,让自己的粉丝们帮他们点赞、关注。
他知道他们会碰见什么。他希望他们的路不再那么难走。
(文中王丽、吴力、顾武、李飞为化名)
来源:中国青年报